青少年眼中的中国 香港大营救——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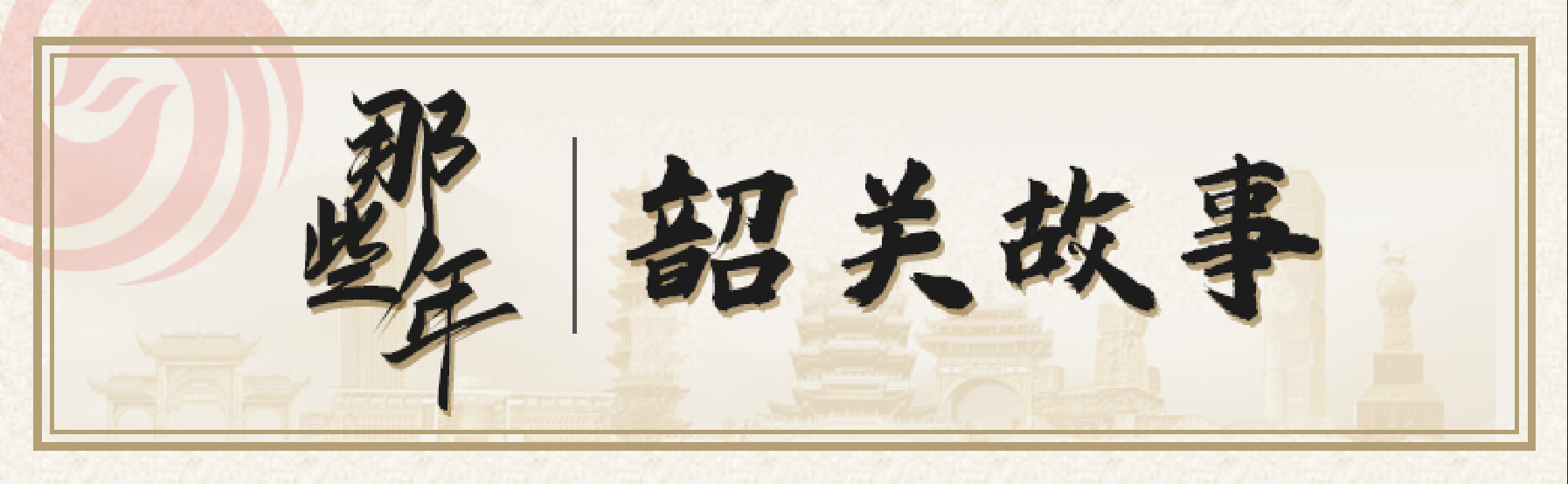
春天的故事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片热土是在深圳开始的。如今,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立,改革的进程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港澳与内地全面互利合作的重点领域,粤港澳大湾区的建成促进三地深入合作,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谈起香港与大陆的合作,不得不提香港大营救。
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大批内地文化人士和知名民主人士处境十分危险。为此,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同志,指示当时正在香港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让他将这些人解救出来。
这次大营救,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被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寻找滞留香港之士
1941年12月8日凌晨,沉睡中的香港突然被凄厉的空袭警报声惊醒。紧接着,日本飞机向这座“东方之珠”投下了无数颗炸弹,爆炸声响彻全岛。当天,大批日军越过深圳河,冲向九龙。十几天后,英国总督杨慕琦在港督府扯起白旗宣布投降,香港沦陷。
香港这个战时的“世外桃源”,随着日军炮火骤至已不复存在。
日军一占领香港,便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并实行宵禁,敌寇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并贴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须到“大日本军指挥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当时,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在内的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处境危险。
中共中央以及南方局对滞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处境十分关心。周恩来立即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让其想尽办法救出这些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于是,中共南粤省委、东江纵队及中共香港市委在八路军办事处的组织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大营救。
寻找这批人士的任务交给了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这位年近 30 岁的年轻人,十分机灵。他跑了几户认识的人士家,都是人去楼空,不知去向。他听廖承志说,徐伯昕是位大学者,又是一位文物鉴赏家,平时喜欢到文物市场溜达,遇有便宜称心的文物,就买下来收藏。他计上心来,去文物市场买了一件文物叫八仙紫金钵,当然这是赝品。八仙紫金钵本是朱元璋的镇库之宝。朱元璋从小家里很穷,被迫沦为乞僧,捧着一只破瓦钵化缘度日,后来做了开国皇帝,为了不忘那段讨乞的经历,特命能工巧匠用纯金打造一只小钵子,上面塑着八仙的图像。
杨康华打扮作文物贩子,在文物市场摆了个地摊,果然,第二天上午,有位瘦高个子的中年人来到地摊前,仔细看了一阵八仙紫金钵并问价,杨康华故意讨价还价,瘦高个子笑着说:" 这是件赝品,不过仿制得很不错,有鉴赏价值。"
根据口音和外貌特征,杨康华估计此人就是徐伯昕,轻声说:" 先生,我有真品,你随我走吧。" 到了僻静处,杨康华见四下无人,当他证实了徐伯昕的身份后,便拿出市委的介绍信,对徐伯昕说:" 日寇的情报部门早已得悉,在香港有一大批知名人士,鬼子必然会对你们下毒手,必须趁敌立足未稳,迅速逃出虎口 !"
徐伯昕一听,脸色大变:" 我们都是文弱书生,手无寸铁啊 !"
杨康华忙着安慰道:" 徐先生不要惊慌,南方局周恩来书记已对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作了重要指示,我们会想尽办法,一定要使你们百分之百地安全地离开香港。目前最紧的是设法找到所有的人,一个不漏,这是关系到能否救出被困人士最关键的一着。因此请你马上先找一部分人,再通过这些人分头去寻找。"
徐伯昕连连点头,说:" 张友渔是《华商报》主笔,凤子主持过生活书店,这两处本是文化人的聚会之地,通过他俩能迅速接上联系。"
杨康华以 " 滚雪球 " 的方法,很快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寻找爱国人士的任务。
与日军斗智斗勇
1942 年 1 月 11 日下午,柳亚子父女、邹韬奋、茅盾、戈宝权、凤子等年龄大体质较弱和有家小同行的近 200 人,陆续到联络点集合,换上东江纵队为他们筹集购买的广东人惯穿的唐装,有的背着一只小包袱,有的拎着一只旧箱子,打扮成难民模样。待到夜幕降临后,由交通员带领出发,在小巷子拐来转去,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拐入铜锣湾。
这时已是凌晨 2 点,东江纵队政委林平早已带领一个排的战士潜伏在草丛里。他见第一批撤离人员已经到达,忙带领他们钻过已剪开的铁丝网内,蹑手蹑脚上了 3 条大木船。片刻,林平发出几声清脆的夜猫子的尖叫声,相隔几十米远的码头上,东江纵队另外几个战士把牵来的十几头水牛同时赶下河里,前头的 4 条水牛预先在牛角上绑了一只手电,按亮了电光。" 嗵 ! 嗵 ! 嗵 !" 一阵河水声陡地响起。这天正好大雾茫茫,相隔两米远便看不清人影,早已摸清敌情的战士又赶紧往河里扔了一阵石头。日军的巡逻艇闻声急忙驶过来,鬼子们以为有人偷渡,立刻,几挺机枪吐着一串串火舌,子弹呼啸着飞向河中的牛群。
这边,林平轻轻一声令下:" 快 ! 划到对岸去 !" 木船在浓重的夜雾掩护下,船工们用力撑篙划浆,飞快地向九龙红勘划去。
第一批撤离人士进入旺角通菜街的联络点后,紧跟着下一站的交通员,混入熙熙攘攘的难民人流中,往西北进发。
通往宝安的青山道、港湾、元朗都是敌占区,为防止与敌人遭遇,他们只有夜行晓宿。这些文弱书生们加上家小,扶老携幼,行走速度很慢,有时一小时只行三四里,那些无法避开的山口、渡口,则必须接受日军或汉奸的检查。
当他们来到宝安山口时,已是 13 日晚上 11 时。这里地势险峻,非通过岗哨不可。岗哨驻扎着日本鬼子的一个小分队,队长叫黑田三郎,另外还有一个排的伪军。游击队的战士悄悄地爬上岗哨左侧的山坡,布了疑兵阵。黑田得到密探的情报,说游击队在虎形山的森林里煮饭吃,他们饿极了。黑田一听,心花怒放,连忙带领鬼子兵和伪军向山上爬去,果然见森林里有一堆火,还隐约传来碗碰碗的响声。黑田忙令士兵卧倒,向火堆射击。只见那火堆瞬间化作数十只熊熊的火把,边走边放枪,在森林里一闪一闪。打了好一阵,森林里的火光全都打灭了。黑田心想,这次游击队完蛋了,他同伪军排长带领士兵到森林里一看,立时傻了眼,森林里一具尸体也没有,原来游击队在森林里故意烧了一堆火,让战士发出碗碰碗的声音,假装在吃饭,然后把灌了煤油的楠竹筒挂在树枝上,放了一阵枪,再撤到悬崖下躲避。
游击队巧妙地调虎离山,岗哨里只留下几个伪兵,他们见来了一大批难民,老的老,少的少,知道是被虎形山上的枪声吓得前来逃命的。香港市委早已准备在先,为受困人士全以化名办好了难民归乡证,伪兵见无破绽,一挥手,让 " 难民 " 顺利通过。
整整跋涉了两天,第一批撤离人员终于到达了白石龙东江纵队司令部,受到司令员曾生、副司令员王作尧的热忱接待。第二天,他们被转送惠阳,再从惠阳送往内地。
胜利救出千余人
第一批受困人士刚刚脱险,日本港督府已发布通告,令所有在港的中国知名人士限期报到,并四处搜捕,却一个不见。于是警戒更加森严,层层封锁了水上陆上的交通。
这天,香港长洲岛码头停泊的 " 安庆 " 号货轮,正在装货卸货,将直达海丰马宫港。日本鬼子连货轮也不放过,码头上军警遍布,虎视眈眈;便衣暗探神出鬼没,凶神恶煞。白天,货轮卸完货,晚上 10 时开始装货,只见许多搬运工人在日寇的刺刀下忙忙碌碌,他们头上披着垫衣,勾着腰背," 吭唷吭唷 " 地喊着号子,扛着一袋袋货物,步履蹒跚,接连不断地往货舱里走。鬼子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夏衍、范长江、金钟华等部分年轻力壮又无家小的被困人士,化装成搬运工,戴着眼镜的摘掉眼镜,混在工人搬运队伍里,肩上扛着麻袋上了货舱,再没有下来,东江纵队为他们准备了路上的干粮和饮水。
" 安庆 " 号货轮由长洲岛入海,绕过港岛南部,驶往马宫港。不料,途中遇上大风,在海上漂流了 5 天,粮食和淡水几乎告尽,幸亏遇上奉命前来寻找的游击队的汽艇,方才转危为安。
至此,在香港的 200 多名知名人士及家属近 300 人全部被安全转移到了大后方。国民政府驻港代表陈策少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等也被救出。千余名滞港的抗日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及家眷、国际友人,在抗日游击战士的护送下从香港神奇“蒸发”而无一人被捕,这是一场胜利,也是一场伟大的抢救工作。

这段历史此后被拍成了电影《香港大营救》上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段历史。不少香港青年看完这段影片后,对此深受感触,并感叹在战争远离公众的年代,这段历史能让人们重温血与火的灼热缅怀,更深刻地了解到在中共中央当年香港这片土地上为人们所做出的贡献,其涌动的英雄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如今,距离“香港大营救”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但那次营救所给与我们社会与时代的巨大影响,却始终发热发光。



